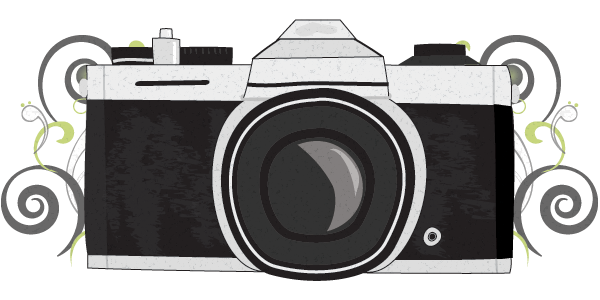还记得吗?那张老旧的云石餐桌上的纹路;那满布气孔,生锈斑驳的铁质折椅。还有正对着大门的,一大面长镜,大楷,朱字——“客似云来”。
几乎每个周日都会和他到这家老餐馆用餐。刚拆下不久的盂兰盆法会的棚架,还未完全清空,极其突兀地就横放在门道上,我们艰难地跨过去,走入店里,点了爱吃的那几道菜,选择坐在最靠里的座位。
已经无法完整地组织句子。面对生人如此,现在就连和他对话也显得艰难。不过,这难题并未困扰我多久,还未解决之前,饭菜就挤下那些酝酿中的话语。烂透的猪脚很顺利地入口,再配上一口熬得经久的炖汤,感觉这些混合着脂肪物与液体的正餐,开始让自己吊上的喉结有些弛暖的迹象。
他不吃。真不吃?想开口问,却冷不防吸入过于干燥的空气,声音在喉头像齿轮尴尬地相互卡住。我赶紧又往嘴里送了一口热汤。他愈发尖削的脸上的那双大眼,像平静的湖面,不起涟漪。这些日子以来,似乎,他愈是瘦,我吃得就愈多。
还真想对他说。“怎么有种你正被我吃着的错觉啊”。
却说不出口。我们正养成一种“对食”的习惯,只有注视着彼此,才能进食。刚开始的时候,身旁的那些人都揶揄我们真“浪漫”,话语间无不夹杂着戏谑与嫉妒的心理。其实,那些人又怎知道,这是我们的关系一旦出现罅隙,当下就会实施的补救之法呢?
最后,我们都会被对方狼狈的吃相给逗乐,和好如初。
谁都无法从谁的身边逃开。
但最近,他却渐渐不吃了。他似乎想要销毁我们之间的约定,于是我抑制不住愤怒的心情,恶狠狠地盯着他看,将食物拼命地往嘴里塞。他似乎并不逃避,一任我盯着他,狼吞虎咽。
一天两天过去,我不再愤怒,反而觉得悲伤。有时候,注视着他,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只得赶紧用饭堵住呜咽的声音。他原本丰润的双颊,日渐消减,像极了被风化侵蚀的礁岩,仿佛就快要见骨。后来才明白,无论我再如何闹腾,也将不会有任何改变。
今天很好,我不再有任何一种明确的情绪。只觉得,他在我面前就好,至于其他的,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应该还会在每个周日,来到这家餐馆,吃一样的菜,坐同一个位置。不会再听见任何的声音,只剩下对视或“对食”。
只有,些微变化的是,大楷,朱字——“来云似客”。
咦?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