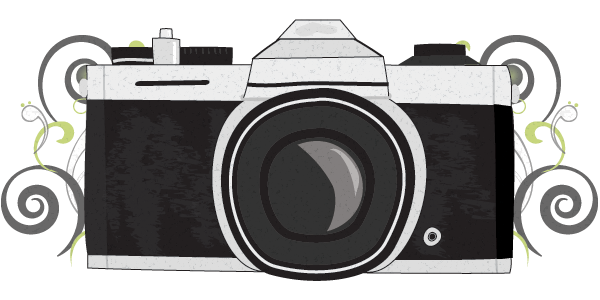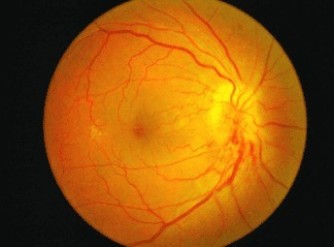“回到最初”
提筆寫下的第一句話。是話,活的字,可堆砌于腔體與齒間的方塊。來,跟著我念誦——呼誒達奧卒誒癡嗚。是的,沒有懷疑地,將自己的軀體輕置于看不見的動線,緩慢地,像放下一塊你深深愛著卻不得不将之消融的棉花糖;讓這四個字逐漸上升,想象它是一襲輕柔的紗,施施覆上容顏,你的鼻樑撐起為支點,它徐徐降下衣襬,與你的出入息正維持著一段恰好的距離。好,再唸一遍:
“呼誒達奧卒誒癡嗚”
你突然感到陌生。初見這句話時,你不覺有異,只覺得這種“回到+XX”的詞組,有些像文藝片的樣板台詞——回到某處、何處、當處?那時,你覺得安在“回到”後邊的那些詞語,只是些可望而不可即的贅言,腹中無物的箴言餅,一掐便碎,只留下了一長串“嘠滋嘠滋”磨人的雜響。你很餓。你從那餅心洞開的缺口處望去,空落落,你便覺得胃給養了一池強酸。於是,你想到了《半生緣》里曼禎對世鈞說:“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就覺得輕鬆了一些。根本就回不去的嘛,為何還要空想。
放緩,像這樣將每一組中每一顆緊密相依,黏糊糊的方塊拾掇出來,歸元成為一種單音。你覺得這有些像混沌未開,氣象閉窒的世界中,初有的音聲,天地人三部音以外,那時已悄悄滋生的小小人的碎語。不是么?嘰里咕嚕之疵詩日彈舌捲舌擦音滑音邊音鼻音喉音閃音顫音海豚音魔音,恆沙數盡,歸元合一,卻只滾成一顆顆單音跳跳糖。“回不去了”你咕噥著說。而今可用的音聲已負荷不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發聲企圖:想說的總比能說的多。興許將來,我們將不滿于臟器所能發出的有限的音聲,而強行植入各類共振器械,量身打造一種,屬於自己的——“個性化”的音聲。這是個追求個性的時代啊。你長噓一口氣。
說起個性。其實,是否存在一種個性尚未發端的時空呢?你我皆疑惑。那應該是個一切歸零的世界,零度的時空,零度的身體,零度的魂識。關於這一切,我所能想象的大概就是那段居於母體膣腔內的時光,倒懸肉身,根未觸塵,長著一根連著命系母體的臍帶,于大水中浮沉。那時候,如入胎未迷,懷著的應是一種喜憂參半的心情,喜的是得此人身,如經中說的,人身難得如盲龜值遇浮木;憂的也是得此人身,愛河千呎浪,苦海萬重波。都是水。于焉你想到了你隨意寫下的一段短句:
“所有生命皆源自于水,別忘了我們曾經生活于海中,後來褪去了鰭,伸手握住那令人不安的流動,開始大口大口地求取,練鰓成頰。從那時起,你就該知道,無論如何進化,我們心底仍住著一座海洋。”
無論如何進化,無論再無法回到“最初”,我們心底仍住著一座海洋。你特別地再加了一些句子,像是要刻意地挑弄一片燈芯。燈不點不亮,話不說不明——一種刻意求深的解說。沒錯,生命的本初,就是在一片大海水中浮沉,我說的是羊水。只是我非賢聖,入胎自然也是恍惚幽冥,歸到一種純粹的零度中。在其中,不知自己活著,卻本能地接收著臍帶輸送而來的養分,生命因此一點一滴地成長。奇怪地,就在這種極難被干擾,最無意識的時空,我卻對於音聲生起了反應。母親說。那時懷著我的她,正在觀看連續劇以排遣極度無聊的坐胎時光。當主題曲的前奏響起,那一段坐落分明的鼓點,我的拳頭竟也隨著節奏在脹大的肚皮中鼓起。關於這段記述,我自然無法驗證母親記憶的真實性,也許這只是記憶與幻想的倒錯?但如果這是真的,那是否說明音聲,得以滲入零度時空的折痕中,掀起死水中的一波漾紋。
娑婆世界眾生耳根最利。我突然想起了這段經句。音聲比起氣味與需仰賴光照方可現形的物體,更能穿越距離的障礙,由此,我們生來似乎就對音聲的波動特別敏感。你說你也如是。你想起剛出生的你,當時窩在嬰兒床中酣睡,半夢半醒間,恍惚聽見一把熟悉的音聲在門外響起,突覺心房觸動,就不明不白地哭了起來。後來,那人慌忙地將你抱起,不住地擠眉弄眼安撫你的失控,那是你父親。你這才發覺,音聲原來可以涵括如此多的信息,像是記憶、面孔還有那更為隱晦的情感。你也還記得,你雙唇碰撞,發出一種類似于爆破,聲大于氣的兩個單音。在遠處的他,像是安裝了一種語音啟動機制的高智能器械,你的音聲瞬息擊中按鈕,他高興地飛奔而來,將你擁住,你感受到了一種短暫的窒息。但比起現在,你果然還是喜歡彼時尚未被語言染污的純粹的音聲。你嚼動著一顆顆色彩繽紛的跳跳糖說。
我何嘗不也是如此呢?被侵染日久的耳根,開始潰瘍而不知,各種音聲像淤泥般,堵塞在窄仄的耳道上,滑膩而充滿毒氣。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的耳朵會退化成為一道沉默封閉的墻。柏林圍墻么?你笑著挑眉。此刻,你又想起那一句:“無論如何進化”。你才覺得當時應是中了那段文字言靈的蠱惑,“進化”原來只是為了對應“水族——人”的過程而寫。其實,人類的進程只會不斷退化,此原來具足圓滿的肉身功能逐一地麻痺、無感直至喪失。我們都無法回到最初了。我們回不去了。你戲謔地模仿了曼禎式的語調,拉著我說。真的回不去了。
回不去最初,自然是回不去了。那居留于母體的無日無夜時光。可後來我想起比起嬰孩稍大一些的稚齡階段,我便覺得那段更有印象的歲月,是否還有往復的可能。那時的我們,開始學會了很多種語言,社會的、家庭的、學校的、小團體的……總覺得語言的樣式永遠抓不透,同樣的意思,當到了不同語境,卻又要轉換姿態,訴說另一種被濾過地,透著光般過於澄淨實質上卻虛偽的語言。可是,一旦在不被其他語境侵擾的,那種純粹的屬於孩童的烏托邦的地方,我們便像蛻下了一層一層的皮,露出鮮嫩無菌的白肉,在陽光底下奔跑。於是,在這種莫名的令彼時仍是孩童的我們的心稍作歇息的情境中,開始嚷著那些我們壓抑已久的單音。在遠處的成人都以為我們著了魔般地說著他們所“不懂”的囈語。那時候,我們開口“啊”,咧嘴“一”,閉口“嗚”,音聲似乎可以穿透一些透明的材質物。像玻璃。當我們放聲吶喊的時候,就不住地顫動。在落日的光照中,我們在後山的遊藝場,釋放一日的積蓄,以預支明日、後日、往後將會愈來愈少的用額般,盡情所以地放肆吶喊,那些原生帶來的純粹的音聲。沒有人能侵入啊,這種堅固不壞的堡壘。你說。
這些用額已盡的日子,似乎是離我們較近一些的“再初”時光。你不由得又想起你幼年時光的貧乏,你記得那時的你同時學了好幾種語言。每一個晚餐后的時段,你的父親、母親、哥哥還有姐姐,都會輪流測驗你的學習進度,他們各操持一種語言,逼著你與他們對話。碰上那些你不會發的音節,他們就一再地要求你練習,直至你學會。那時候,你覺得你稚嫩的口舌無法操弄那些音節反復詰屈聱牙的語言,你一直想要逃出家門,雖然你在外並無可寄宿之處。直到有一天,你的哥哥正在示範一列你無論怎麼學也學不會的語言,你再也忍不住了,終於釋放你那壓抑已久的頭聲——“啊”!巨大的拔尖像是震響了某個輕質的餐具,你的家人似乎都嚇了一跳,周圍的溫度逐漸變得冰冷,你一度以為桌上的冷盤都快要給覆上了一層冰霜。就在這時候,你突然覺得右臉頰飛上一陣火辣辣的熱燙,你母親給你掄上的一記耳光。現在想起那時候,我才覺得音聲是有無陷的可能啊。你突然失笑。你說那時的你像被觸碰到按鈕的狂暴機械人,你想到了你父親。你突然在偌大的飯廳間繞走,接著發狂似地叫喊,嚎哭,更推倒了試圖壓制住你的父親。你不曉得當時何以能發出一種近似核爆的巨大轟鳴,在那一次的暴走后,你整整沉默了一兩天,甚至將自己圈禁起來,而後來他們也果然不敢再過分地逼迫你。但你說那只是因為他們怕鄰居碎嘴,礙於面子而作的決策。
嗯。所以你明白了為什麼我們要將“回到當初”念成“呼誒達奧卒誒癡嗚”了么?你神色黯然,卻像是知道了其中的一些什麼。看著你,我想起小學畢業的那一天,我們一群濃妝艷抹的男孩女孩,白襯衫上的右口袋別著一朵假花,排排站在台上。我記得有個男孩兒,因為趕著回家拿取某個重要的證件,而錯失了人生唯一一次的小學畢業典禮的登台機會。當時候,在台上的我們並不覺得這是多大的事。只是 ,站在第一排的我,清楚地看見了那個男孩兒平日活潑的臉上,重重地罩上了一層死灰之色。看不見的悲傷。隱于日常之下的絕望。錯過了,便不可重來的語窒。音樂響起,台上的我們聲勢壯闊地唱起了驪歌,並且安分地將每一句歌詞唱得極其完滿。字正腔圓的那種。緣不能念作緣,要念成魚+安,才能令人聽得字字分明。大概從那時候開始吧,我總想將每一個黏膩濃稠的雙音節拆分開來,儘管以成人的音聲復誦這些單音有些艱難,畢竟我們再不是無所畏懼的稚齡時代。明月幾時有,千里共嬋娟的娟要念成居+安吧?你開始聯想起相關的字眼。
“回到最初”。所謂的“回到”果然是個假靶。你又說。我們只能追溯最初的音聲,繼而再初,然後……然後呢?初于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我想起了另一段經句。少年時期的我,似乎從“入流亡所”開始便能感受到心底一絲微細的漾動。其實,我並不如你想象般了解這段文字的“第一究竟義”,宗門巨匠那些直指人心,本真如如,不容質疑的真諦。只是,當看著這些迥異于日常語彙的名相,我才覺得稍稍能脫離那日漸壯大,幾乎已將心中僅存的那些蹦跳的單音消磨殆盡的龐大反復的語言困境。開始的時候,是依照自己的直覺來認識經句,像在每一個午後,無有思想地唸著一段段優美的韻律。據說,當年天竺貝葉所載的長頌經句更能表現出,音節的鏗鏘,我想象那時候那些尚未化為中文的悉曇字母,在人體內的七脈輪中反復流轉,最後再隨著中脈,衝出明點,化散于虛空之中。阿、烏、吽。天地人三部音的華麗紛呈。只有在那午後僅有的時光,從半天的疲憊中走出,將自己鎖在房內,才能獨自領受內在巨大的獨語。只有這樣,我才覺得得以守住一些害怕失去的,與即將逝去的那些。因此,當讀至“入流亡所”一段的時候,便覺得這其中隱含一種生死流轉的意味。雖然其原意為說明從聞思修的次第進修步驟。這種不斷重複的內在獨語的時光,佔去了我少年時期的很大一頁篇幅。可能得以看作彼時整個時期的速寫。因為,為了對抗那排山倒海而來的語言大雜燴,我所用盡的時間絕不比你想象得少。譬如,當周遭響起一大片流行音樂的音聲,那足以將人淹斃的靡靡音海;那遊戲機體反復播放的很“燃”的那些巨響;那些偶像劇像排得緊緊的分子粒子的連珠炮台詞。你怎能不靠一些遠古地、單一地、更為符合作為一個人的聽覺承受量的音聲,來維持那隨時潰散的意志與念想。一直到今日。
“回到最初:呼誒達奧卒誒癡嗚”
一直到今日。也許是應對了機緣,我嘗試了一種直覺提煉法,一種將腦中首先浮現的一句話寫在紙上,以作為一個人一天最大的命題。“回到最初”。我寫下了這句話。與其說這是我今天的,不如說這是我此生將一直行將不倦的最大的命題。你跟著我將這些連綿的字句拆分成一個個單音,也許還能分得更細,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細碎的音頻。一種螞蟻的私語或細胞為了表現某種情緒的共振。你說,我們是再也無法回到最初。你感受到了作為一整個不斷變化時代洪流中的蜉蝣,我們不能抵禦廣大音聲流的急遽變幻。只是,我對於這些龐大複雜音聲終將在一日,分離歸為一顆顆單音,或更進階地化為一種音聲“流”,真正意義上的,“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一種更能提升靈魂愉悅度的音聲,仍投以巨大的盼望。
到那時候,我想,誰也再不會感到陌生。畢竟,那是我們最熟悉的曾經。